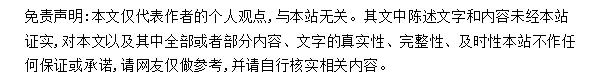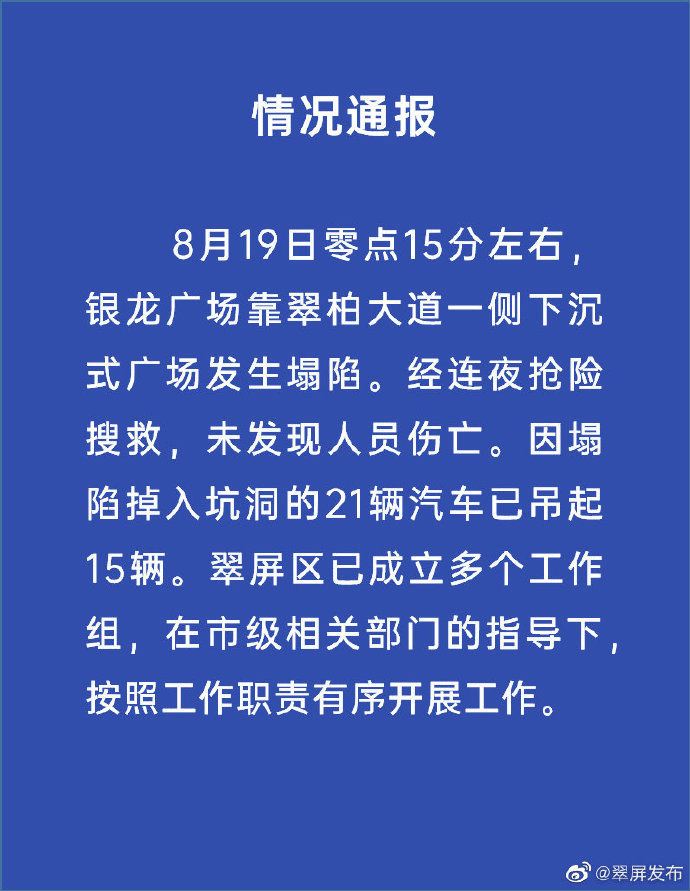1931年2月7日,寒夜,“龙华二十四烈士”血洒刑场。内有五位“左联”青年作家柔石、胡也频、李伟森、冯铿、殷夫。当时,上海的报章都没有报道此事。两年以后,鲁迅先生怒而撰文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,公开纪念“左联五烈士”。
2021年2月7日,也是一个寒夜,大型原创话剧《前哨》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首演。
壮别九十载,今日迎君归。剧中,柔石所追求的“青年不再恐惧,不再沉默,能够尽情地读书,尽情地创作,尽情地去爱”的“一个新的世界”,早已成为现实;一群“90后”演员,去追寻九十年前一群同龄革命者的精神足迹及其思想灵魂。在时间的两端,烈士从模糊中清晰起来,意义在比较中彰显出来,足以令当代人陷入历史的沉思。剧中的青年研究生姚远吟道:“九十年前,他们不肯顺流而下,用青春和信念去解时代的镣铐。九十年后,我们追踪他们用鲜血拓下的足迹,以初心召唤未来的征途。”其义昭然。
两个寒夜,似乎是历史的对接。
此时此刻,一个是史学的真实,一个是艺术的呈现,使剧场成了纪念场所,使演出成了纪念仪式。
一
《前哨》是一部关于革命和青春的话剧。此类题材作品已然不少,堪称经典的却不多。或是主题稍显生硬,或是人物稍显单一,或是叙事稍显平铺,在美学的等级上,从真实的发现,到道德是非的发现,再到社会必然规律的发现,至人类价值的发现,拾级的幅度总是不大。
《前哨》有自己的追求,它善用优势,也规避弱处。该剧的主人公——一群花样年华的文学青年,身处文学狂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激情满怀,五彩缤纷,赋魅故事颇多。作为该剧的扮演者,青年演员可以轻易捕捉到青春的气息,他们的朝气、梦想甚或稚嫩。然而,斗争的严酷,精神的炼狱,“墙外桃花,墙内鲜血,彼此照映,尤其残酷”,是演员们所陌生的。
在此,角色和演员都指向了一个深邃的意旨——信仰,只有它的合理化或者合法化,赋魅才能建构,并放大它的效应。
该剧运用一个巧妙的结构方法,将故事发生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、剧本创作时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演出进行时的当代,进行时空“穿越”,以当代演出者的“发问”,不断向前逼近那两个年代,深勘两个年代的信仰“矿井”。上下求索,逐渐触摸历史的褶皱。剧中,青年研究生左浪表白:
“我们现在看的资料已经足够我们消化了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,从人物的内心出发,去感受他们。”
“这五位烈士都是知识分子,不革命生活也过得去,像殷夫还可以过得很好。但他们为了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出去革命了,他们为的是什么?他们跟我们一样,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那他们被抓,被关进监狱的时候,会想些什么?他们害怕吗?恐惧死亡吗?想过退缩吗?我觉得,想接触他们的内心,得想办法真正进入他们的时代去感受他们的温度。”
这是两个时代同龄人之间的“信仰”考问,它提出了一个“温度”理论,表明了该剧的“信仰”感受不是教化式的,力避历史隔膜和高度遥望,而是用温度去感受。
这种探讨式的“信仰”叙述,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,是温暖的,也是入心的,主题、人物和叙事由此镶入,并具有了价值的意义。这是话剧《前哨》的人文姿态。
如此,观众能够理解殷夫与国民党高官亲哥的决绝,懂得柔石和冯铿牺牲之前的爱情呢喃,并为如下的思想境界深深动容:
“如果我们出不去,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,这里有过这样一朵小小的桃花呢?”
“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。未来的花总是每年都会开放的。”
如许,才有文人式的飘逸生命感怀,“春去秋来,岁月如流,东奔西走,游子徒伤怀;杭州苦读,北上求索,故土彷徨,海上风华,光景宛如昨”。这是纯净人格的极致洒脱。
叙事之间,穿插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是剧本创作时,却是一个未完成本。剧中的两位青年研究生问询:“我们现在有个问题,当年编剧为什么没有写完就停笔了?我想知道他遇到的困难,这样才能知道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。”“这都三十年了,当年的编剧是不是都把这个剧本忘了?”这似乎是赘笔,却将故事发生时和演出进行时连接起来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另类民国作家重新红火,“左联五烈士”研究没那么多受关注,故而“没有写完就停笔了”。三个时代,对待烈士的态度形成一个曲线,该剧亦成为九十年中国精神史一个侧面的生动演绎。
二
《前哨》编剧黄昌勇是资深文化学者,研究“左联五烈士”有年。他认为:“不必一味追求戏剧冲突,重点是如何展现五个青年用文学开拓战场的状态。”他去传统的戏剧性,以主人公与时代的整体冲突作为主线,追求另类的大“戏剧冲突”。
该剧的舞台意象,可谓“美”。从主人公人格的美,扩展到舞台语汇的美:大处写意,小处写实,该淡处瘦,该浓处厚,古典与现代融和,沉重与空灵汇合,慷慨与冷峻交替。
演出中多媒体的使用,与整个舞台空间、表演意韵相生相映,演员可以自由穿梭于各个不同时空以及场景之中,思想、历史与城市空间转换行云流水。专为戏剧拍摄的电影片段,及采用柔石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《早春二月》的片段,也为此剧增添了一种与历史互文的艺术维度。
历史的时空,角色的服饰是写实的,当代人物却颇有卡通意味,展示一种现代主义的时尚格式。在演员视觉上,它提示了一种代际的分野,在一个代沟(代际频次)大于地沟(地理沟壑)的时代,代与代之间必须传承,让思想文脉绵延。剧中,还有浪漫的超现实表现手法。丁玲寻夫,万分焦急之中,舞台上出现了几个丁玲,敲门,大喊,疯跑,穿梭。龙华桃花林一场戏,风吹花落,硕大的花瓣漫天飞舞,几乎将演员淹没,“左联五烈士”和丁玲互掷花瓣,玩闹起来,如梦似幻,仿佛非在人间。
我时常想,一代有一代之戏剧。今天,观众审美心理变了,是否已有新剧种诞生之契机?犹如当年“西皮”和“二黄”融汇而成京剧一般。在工业4.0时代,多媒体戏剧、实时影像戏剧,已在舞台展现它的魅力,契合当代观众的接受美学,它或许是新剧种出现的端倪,可以称之为“新影戏”。
显然,《前哨》的话剧新样式已跨了一大步,转媒体、融媒体运用娴熟,展示出舞台之美的绚烂。这是《前哨》的美学姿态,只是需要理论家的呼应和阐释。
三
话剧《前哨》与龙华相关。
这里,曾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,“墙外桃花墙里血,一般鲜艳一般红”。
话剧《前哨》让我想到,红岩和雨花石,因为小说《红岩》和其他系列雨花石文艺作品而为全国人民熟知,龙华却缺乏与小说《红岩》等级匹配的相应作品。那么,话剧《前哨》的出现,是否能产生一种催化效应,以后有更多反映龙华革命故事的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和小说出现,让人们更好地知道、了解龙华的历史?
这是话剧《前哨》的城市姿态。由此,也扩展到整个上海的红色地标。其间又该有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,是上海文学艺术创作的偌大富矿。
近年,上海在这方面的文艺创作成绩不俗,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杂技剧《战上海》已成全国新主流作品的美学标杆。《前哨》作为话剧样式,还将不断修改公演,应该努力与前两部一起,共同构筑红色文化的上海美学样本,讲好上海故事,也使它本身成为上海艺术发展史的一个亮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