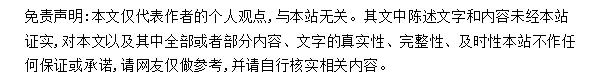文丨聂雄前
壹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1975年10月底,鹅公坪来了一大群河南人,十来部驴车,五十三个人。驴车从春婶叽家门口排到家胜师傅家门口,他们竟然不走了。
他们应该是走了一个通宵,看到鹅公坪这块风水宝地就停了下来。这块大坪有一点点像他们北方的平原吧?秧冲中学和秧冲供销社肯定让他们惊艳了吧?他们一大早开始把驴分成两拨,一拨放在连山塘喝水,一拨放在面公塘喝水,喝得那个痛快啊!我们这些放牛的、拾狗粪的,赶紧掉头回家禀报父母,说来了好多好多的外地人,不得了啦。然后,他们就在供销社东边的坪上,拿出铡刀铡草料,一堆一堆放在每一棵苦楝树下面,把驴子牵过来固定到树干下吃草料。队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出来,大感惊讶。
正是收割晚稻的季节,秋高气爽、晴空万里。朱来新队长开始交涉,问他们是哪里来的,问他们想干什么。基本上是鸡和鸭讲,来新队长脸红脖子粗地说:“只听懂‘河南’两个字。我就不相信了,他们难道是河南来的?几千里路啊,走哒会走死。”他手一摊,你们到底要怎么办啦?一个老成持重的河南人,拿出他们大队、公社两级的讨米介绍信,上面竟有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。为国分忧,自力更生”的字样,有大红公章。来新蒙了,就问老队长锡福先生的主意。锡福先生老谋深算,说:“这个事情很麻烦,搞不清来路也搞不清去路,话也听不懂。话听不懂还好办,叫秧冲中学会讲普通话的老师就搞定了。关键是这个公文这个公章是不是真的?俺老师①觉得要到大队去求证,到公社去求证,才搞得清楚。俺老师就只能讲这么多了,你看着办吧。”来新一跺脚:“锡福先生你直接告诉我到大队到公社好不好?要出工了嘞。请你老人家派工,我现在就到大队去,到公社去。”锡福先生就讲,你的铁哨子给我唦。
锡福老队长重温了他的队长梦。他神气活现地派工,百多亩田、几十块地都在他心中,哪几个踩打稻机,哪几个递禾,哪几个割稻,哪一个出桶,严丝合缝。今天从哪丘田开始,到哪丘田结束,都按照插秧时的顺序。哪两个用龙骨大水车,哪一个用手柄水车,具体到人……派工一组,他就吹铁口哨催一组,丝丝入扣。派工完毕,他就背着手在鹅公坪各个做工的现场逡巡,谁做得不到位,他就指导一番。来新队长从大队走到包家堂,来回也就个多小时,但快两个小时了还没回来,锡福先生就讲,“鹅公坪有麻烦了”。又过一个小时,锡福先生就讲,“鹅公坪有大麻烦了”。中饭吃过了,来新还没回来,锡福先生就慌了。
下午三点多,来新终于回来了,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七八个干部。
锡福先生拿着这个铁哨子,就像拿着烫手的山芋,利利索索把铁哨子还给来新:“来新队长,现在怎么办?”来新说:“你老人家找各家各户来个当家的,我去找那个有讨米公文的河南人,到同新主任家开会。”
四点钟正式开会。同新叔叽的大堂屋坐得水泄不通,大队彭如凤书记一一介绍领导,有龙田区的副区长,有公社王喜顺书记,有信用社王同新主任等七八个人,然后,请王喜顺书记做重要讲话,大体意思是:一、来到鹅公坪的这些河南人民,是我们的血肉兄弟。他们受难受灾了,中央很重视、湖南省委很重视、双峰县委很重视、龙田区委很重视,因此,柘塘公社党委必须重视,秧冲大队要更加重视。二、向河南人民表个态,你们既然看中了鹅公坪这块风水宝地,就饿不死你们。我们公社会发个通知,见河南的人民讨米就直接给一升。我们有二十三个大队,你们分头讨米,不要五十几个人一起讨,行不行?那个拿着公文和公章的河南人就举手,说听不懂。喜顺书记就说,不好意思,我带了播音员来了,她会讲普通话。播音员一复述,河南人连连点头。三、给鹅公坪乡亲一个要求,不准欺负河南人民。谁欺负河南人民,我们就开万人批判大会批斗他。哪个人没有饿过肚子?哪个人没有过病痛?你们要将心比心,何况公社对鹅公坪乡亲有优惠措施,一个月每家只捐一升米,算个㞗?播音员复述一遍,河南人说湖南人民仁义。四、同新同志高风亮节,已向县委区委公社保证做好河南人民的安置工作。我们完全相信他的能力和水平,你们一切听从同新同志的安排。播音员又复述了一遍,同新叔叽就和那位河南老乡亲切握手。最后,龙田区副区长宣布,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,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。会就散了,不到一个小时。
留下来的干部只有同新叔叽。同新叔叽双手抱着自己的头不断地捋头发,捋了十来分钟,就站起来,对来新哥讲:“你去秧冲中学找个会讲普通话的老师来,然后带着那个有公文的河南人来。我去看个现场,我们在供销社的坪里会合。”
同新叔叽从春婶叽家门口数起,数到家胜师傅门前,驴车总共有十三部。他蹲在供销社的地坪上,默了一会儿神。来新哥带着两个人过来后,他已胸有成竹。
同新叔叽讲,先把十三部驴车寄到供销社的院子里,只有供销社的院子里有铁门上锁。他指着河南人问,经秋娥老师一翻译,河南人同意了。
同新叔叽指着驴车上的被窝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继续问,你们分几个屋场住?你们的驴子怎么养?你们在哪里吃饭?……问了好多好多个问题,秋娥老师向河南人一个一个求证,然后转达给同新叔叽。很简单,就住在同新叔叽家里,驴子就放在聂家屋场和供销社东边地坪里养,吃饭也在同新叔叽家里做。同新叔叽差点晕倒。河南人看到这场面,就要秋娥老师强调,不会给同新叔叽一家添太大麻烦。
同新叔叽哭丧着脸,想死的心都有了,他说:“冇得了啊,五十三个人,我那里怎么住得下啊,我还有老娘啦……”来新队长咬咬牙说:“我把我家的堂屋清出来,你不急。”同新叔叽横下一条心,就领着背着被包、提着日用品的五十三个河南人到他家去了。
同新叔叽说,实在住不下了,分到几个屋场好不好啊?河南老乡你进来看看。
河南老乡摇手,坚决不进门。然后,震撼人心的场面就出现了。
同新叔叽的堂屋门与我伯伯家的堂屋门对应,中间是一块四五十米的地坪,残破的青石板古驿道就在他家门口穿过。同新叔叽家有九口人,西边一排横三间,靠南的一间是同新叔叽夫妇住。六奶奶还在,带着两个孙子住中间房。四姐妹住靠北的前房。向东延展,就是南北通透的厨房、大堂屋和侧屋。主屋和牛栏、猪栏、柴屋、茅厕隔一道沟,靠着南边的马路。
同新叔叽请河南老乡进屋,河南老乡坚决拒绝。就看到十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在屋檐下面的台阶上开始铺塑料薄膜,薄膜上铺草席子,草席子上放被窝。十来张草席子铺下去,就恰好把同新叔叽的屋檐底下排满,只留下西边的前房门和堂屋门进出。
同新叔叽一看这个阵势,眼眶就湿润了,颤颤巍巍地提出三个问题。
“你们是不是一个家族的?”
“大哥,我们是一个家族的。我们亲兄弟姐妹七个,生了二十九个子女。堂兄弟姐妹九个,生了四十多个子女。老人家都没来,没满十岁的也没来,靠政府救济。”
“我刚刚才知道你们那边发了水灾,你们哪一天起程的?”
“发大水,死了好多好多人。老天照顾,我家住在岗上。8月18日起程的。”
“你们一直睡在屋檐下?十来张草席睡不下啊。”
“大哥,你帮了我们大忙了,我们一直睡屋檐下。晚上驴子要几个人看护。”
同新叔叽默默地进屋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,同新叔叽看到屋檐下已经干干净净,两个大嫂在侧屋的屋檐下用几块土砖架起了一口大锅煮饭,两个小伙子牵着驴子在面公塘喝水刷毛,塘基上有三个十来岁的小孩背着柴火正走过来。同新叔叽问两个小伙子,其他的人呢?小伙子指着供销社那边伸出三个指头。再问,其他人呢?小伙子回答,找工、讨米。
按公社的要求,同新叔叽在家观察河南人五天,看需要解决什么困难。不到三天,他就心里有谱了。他给公社领导讲了四条:第一条,他们真的不添麻烦,没有一个人进了我的屋,请都请不进,素质很高。第二条,他们讨米都从远处讨起,他们聪明啊,去讨米的都是黄皮寡瘦的堂客和小孩,不像罗富生算命从近处算起,老了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第三条,他们真的吃得苦耐得劳。那些男的到处找工做,哪家哪户要担煤炭,哪家哪户要起新屋,走马街到梅山坪要修条机耕路,他们都门儿清。当地人做一天一块钱,他们只要六毛钱包饭。就这么几天,五六个小伙子就找到工了。领导你们想,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公文上讲的“自力更生,为国分忧”啊?第四条,讲给领导你们不会信啊,我不知道他们五十多个人在哪里屙屎屙尿啊,到昨日才知道,他们早晨五点半之前就偷偷地屙了呢。那个河南老乡忸忸怩怩问我粪缸快满了,怎么办?我说交给队上还有工分嘞。
喜顺书记一脸沉重,说还有什么困难没有?同新叔叽就讲:“有困难,二十几条驴子要吃稻草啊要吃糠饼啊,我们生产队负担不起啊。”书记立马写了一个条子,“鹅公坪周边生产队:每个月支援更古生产队一大板车稻草一百斤糠饼。王喜顺手书”。同新叔叽喜饱了,说:“我拿到这个尚方宝剑,什么困难都没有了。”
阳历年底,同新叔叽终于把所有河南老乡请到堂屋和侧屋里打地铺了。还有五六个小伙子就住在牛栏顶棚的稻草堆里,这是河清哥哥昨天告诉我的。
除夕夜,王喜顺书记带着七八个干部慰问了河南老乡,提了一大坛烧酒,提了三十斤肉,在同新叔叽的堂屋里摆了八桌。干部们只给河南老乡夹肉,只给河南老乡敬酒,自己只吃蔬菜。
清明节的第二天,王梅娟告诉我,昨晚那些河南人在偷偷地哭。
1976年5月中旬,青黄不接的日子快过去了,河南老乡一夜间就消失了。六奶奶在我家坐了一下午,一直在流眼泪,她说他们家准备的东西,河南人都没带走。
“1975年8月8日凌晨1点30分,由于超强台风莲娜导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,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漫溢垮坝,六亿多立方洪水,五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下。由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作序的《中国大洪水》中这样描述这次灾难:‘超过2.6万人遇难,倒塌房屋596万间,1100万人受灾,1700万亩农田被淹。’”我搜索出这段文字,问河清哥,在你家住了大半年的那几十个河南人是不是1975年发大水来逃荒的?河清哥说,是的啊。是不是驻马店的水库垮坝了啊?河清哥说,是驻马店,确实是驻马店。
我永远记得讨米公文,永远记得六奶奶和同新叔叽母子俩的善心。
我永远记得,春风怒号中的鹅公坪,竟然在一周内生了三只小驴儿。
我永远记得,我家地坪上的驴粪蛋儿,一点也不臭。“驴粪蛋,面儿光,里面全把渣草装”的童谣,从河南人的口里哼出来,我很快就学会了,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①俺老师,锡福先生对自己的称呼,略带一些不太谦虚的味道。
贰
1976年3月中旬,春雷滚滚,万物复苏。我牵着那天早晨喂得饱饱的大水牯,晃晃悠悠地走向更古大塘的塘基。丝丝春雨打在我的斗笠上,放眼秧冲那一大垄田野,云山雾罩、春水满溢。每一丘里都有一二个乡亲在削理田墈边的荆棘和杂草,调整月口的水流状况。我把牛绹交给塘基下面第一丘大田里的鸿文大哥,他马上开始新一年的春耕生产。
砰砰两声闷响之后,一声凄厉的喊声就响起:“冇得了啊,雷打死人啦!”我和鸿文大哥抬起头一看,塘基上竟冒起一串青烟,赶紧就跑上去。一个男的四仰八叉躺在地上,鼻子和耳朵都在流血,一只箩筐装着大半筐米完好无损,另一只箩筐倒了,有雷火烧灼的痕迹。附近田里的人赶过来十几个,来新队长飞也似的从晒谷坪跑过来,第一句话,“幸亏不是我们鹅公坪的。”第二句话,“老三(鸿文),你赶快去叫美坛子(赤脚医生王和美)。”第三句话,指着塘对面的更古大屋,“赶快去拆副门板来,抬到屋里去。”
我惊出一身汗,几分钟之前我还站在这里。要是我还让大水牯多吃一会儿草,雷可能就劈到我呀。我打飞脚回家,急急忙忙吃了几口饭,背起书包就跑。整个上午都在后怕,中午放学回家就问我娘:“那个遭雷劈的人好了吗?”我娘说:“送到区医院去了。”
我娘已听说我在现场,不断地给我抹阳火,一直在念叨:“你没有做过亏心事,不要怕啊。雷公老爷有眼睛的,不会乱打人。也不知是什么鬼,这几年,年年都有听到雷打死人的消息。去年草塘广播电线泄火打死一个你记得不?前年姚家桥打死一个在田里你记得不?以后一打雷你就赶快回家啊!”她突然站起来,把水缸边的广播盒子下面的地线一把扯掉,说以后不听广播了。
第二天下午,和美哥专门来到我伯伯家通报昨天早晨的雷劈事件。他说,从大队部到更古塘就二里路,骑单车就十分钟。那个人一看就不行了,耳朵鼻子都流血。但还是给他做了二十多分钟人工呼吸。后来,心跳基本正常了,心窝子也热乎了,他就只好叫了两个人拖着板车送到区医院,他也一直跟着。到区医院也就个把小时,医生听他介绍的情况,就说处置得对头,然后就开始抢救。谁知老天爷不开眼,打开氧气瓶输氧,才发现没有氧了,只好打强心针。等到县里的救护车送氧来,就是下午二三点了,人已经变了相,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拖到晚上八九点就死了。人是峡山塘的,可惜了。我伯伯讲,真是碰了鬼了,这几年硬是不安生,年年都雷打死人,和美你小心一点啊。
1976年5月,河南老乡离开鹅公坪第三天的大清早,我提着粪筐和小铁耙去晒谷坪牛栏房放牛,从屋后门上竹山就看到一泡狗屎,很惊喜。再走十来步,又看到一泡狗屎。走到晒谷坪边上也就一百多米,竟然捡到了五泡狗屎,我那个欢喜啊。马路对面是供销社的东边地坪,一只狗在一棵苦楝树下撒尿,我走过去,树下还有一泡狗屎,再看前面一棵苦楝树底下,又有一泡狗屎。一直走到第六棵苦楝树,都有一泡狗屎。供销社东地坪的中间立着一根巨大的电线杆下有两泡狗屎,运货进出的铁门两边有两泡狗屎,我的粪筐就差不多满了。我提着一粪筐的狗屎,急急忙忙倒到我家的茅厕里,告诉我娘:“今天到处都是狗屎,不知碰到了什么鬼了。”我娘说:“你是不是走狗屎运了。”我知道,我娘不会相信。
我提着粪筐和小铁耙直奔牛栏,往东走,就是李家屋场。李家的地坪边有条水沟,沟上铺着一块大石板正对着李家堂屋,上面有一泡狗屎。再往前走二十多米就是秧冲中学的校门,校门口竟然有三泡狗屎,我急急忙忙用小铁耙把狗屎收拾到粪筐里,心里就发虚了。恰好钟安提着粪筐和小铁耙从长斌屋后走过来,一看他的粪筐也有大半筐狗屎,就问他,今天怎么啦?钟安说,出门之后到处是狗屎,天天都是这样就好了。然后,我和钟安就看到鹅公坪经常拾狗屎的十来个小朋友,粪筐里都有丰硕的成果。
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,所有拾狗屎的小朋友都满心欢喜地告诉父母:“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狗屎。要是天天都这样,就发大财了。”秧也插完了,春风杨柳万千条,家长们半信半疑地提着粪筐和小铁耙去拾狗屎,确实还大有收获。有人说,这要有多少狗啊才能拉出这么多屎啊。有人说,是不是四面八方的狗昨夜里在鹅公坪开大会啊?他们很疑惑,周边的生产队都很正常,甚至正常得没有一泡狗屎。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,这是第一回啊。中午我放学回家的时候,还看到好几个乡亲提着粪筐和小铁耙在寻找狗屎。
没想到这天深夜成百上千只狗集体暴动,吼天吼地,从春婶叽的家门口到农机站,马路上都是狗。鹅公坪家家户户把前门和后门关得严严实实,并顶上杠子,惊恐万分地听着狗们的大合唱,瑟瑟发抖。大概闹到寅时,狗们就一群一群撞门,二十来户人家的壮劳力都手拿扁担在堂屋候着,生怕冲进屋来。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,也是第一回啊。卯时一到,狗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一泡狗屎都没有留下。
那天早晨万籁俱寂,我打开门习惯性地发出一声呼哨,宋家的桩子竟然没从狗洞爬出,大喊一声“桩子”,它才窸窸窣窣地出来,狗王的威风完全没有了。我走到晒谷坪,就看到来新队长和朱雪云、秦和民、罗义生等在讨论,每个人都拿着一根棍棒,脸色严峻。然后锡福先生、李家兄弟、河清哥等都来了。先看秧冲中学,几位老师已围在大门口看狗们拍门的脚印,密密麻麻、触目惊心。胡老师说,昨夜里外操坪至少有一百条狗,吓死人哪。再看秧冲供销社,大门上的狗脚印密密麻麻有一人高。在往农机站的路上,我奶奶的娘家侄孙子李定胜老远老远就大喊:“吓死人啦吓死人啦,赶快去请师公驱邪啊!”
幸亏中午时分,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省地(市)县的关于预防控制狂犬病疫情的情况通报,鹅公坪乡亲才醒过神来。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开始了,上面的要求就是杀无赦。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联动,每一个生产队组织一个十二人的打狗队,每一天生产队申报给大队,大队申报给公社,公社申报给区公所,区公所申报给县政府。我哥、河清哥、雪云、杏秋、凤成等打狗队成员,基本上使用硬攻和智取这两个手段。硬攻就是一锄头敲死、一棒子打死、一网子叉死,用来对付生产队熟悉的狗。智取就是一小块肉里裹一个大鱼钩,一个肉包子里打一针敌敌畏,对付外来的野狗。不到半个月,狗们就销声匿迹了。鹅公坪家家户户享受着狗肉的盛宴,狗肉的香味久久飘荡在鹅公坪的上空,什么狂犬啊什么疯狗啊,都抵不住美味的诱惑。
我把桩子藏在伯伯家界基靠里面的壕沟里,背了一捆稻草给它做了一个简陋的窝,每天偷偷送一个饭团。三天过去,五天过去,十天过去,桩子真的疯了,对我都开始狂吼。打狗队赶来,桩子夹着尾巴狂奔。后面的几个晚上春风怒号,我隐隐约约听到桩子凄厉的狂吼,在面公塘对面的油茶树林,在我家的竹山上面,在晒谷坪上。
真是一条好狗。
以后,我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好狗了。
叁
湘中丘陵地区是一个神奇的所在,那种红色的泥土血红血红。春日温煦的阳光下,我坐在鹅公嘴我爷爷奶奶的坟头上,听着阳光和大水牯一起吞噬青草的声音,无尽的踏实感油然而生。三四百米远的鹅公杯其实就像一个血红血红的馒头,在绿油油的秧冲田塅里金光灿烂。无数的岁月,无数的乡亲,以为全世界无数的山河都是一样的。殊不知,红土地在中国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低山丘陵区,包括湖南、江西两省的大部分,以及滇南、鄂南、粤北、闽北等地。我相信,红土地的独特性发现应该就在一二百年之间,吾乡罗尔纯先生(1930—2015)对故乡的牵挂所激发的伟大创作,让湘中的红土地成为一个与热血媲美的象征,让红土地上的人文自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独特风景。
画家罗尔纯(1930—2015)
1946年,罗尔纯报考苏州美术专科学校,校长颜文樑是一位留法的美术教育家,他的作品深受印象画派的影响,在艳丽的色彩中弥漫着光与影的颤动。五年刻板的古典主义教育,罗尔纯赢得了学生中最高的荣誉,但是他常常自问,这就是艺术的全部吗?他有湘中人的执拗。毕业后,他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搞创作,1959年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任教,被吴冠中先生的艺术作品深深吸引。在与吴先生的交往中,罗尔纯潜伏了十年之久的思考被激活,儿时红土地上的点点滴滴排山倒海而来。在当年的暑假里,他回到阔别十六年之久的故乡。
家乡丘陵上的红土,染红了他的鞋底。家乡明晃晃的太阳,激发了他的灵感。罗尔纯躁动的内心突然就得到了故乡的抚慰。回乡的所见所闻,后来陆续出现在他的画布上。以此次回乡为起点,他画面上的红色越来越强烈,就像壮士的鲜血。红色面积也越来越大,大到几乎充满画面。他干脆使用纯色的红直接涂抹在画布上,用刀刮、笔抹,抒发他对故乡的感恩。罗尔纯说:“我就是我自己,不管飞多远,魂牵梦绕的还是湘乡的那片红土地。”
罗尔纯油画作品
罗尔纯的《红土》《九月》《奶奶和孙子》《山村牛群》《村头》《村口》《一棵树》《树林》《山间小道》《古寨暮色》《土坡》《红墙》《夕阳》……都是强色彩和强情感的伟大杰构。值得深思的是,他的这些伟大作品,大多是春风怒号、冰河解冻之后抒写的。湘中的红土、村庄以及广袤的土地与明亮的天空,被他全身心融入描绘对象的世界里。色彩是他的全部美学、道德以及人性的追求。无论是鸡冠花、植物和动物、红土地上的乡村风景,还是少数民族妇女和湘中农民的各种形象,都满溢情感的强度,让春天和生命成为主旋律主基调。看着春风怒号的《一棵树》,看着《九月》温驯内敛的小姑娘,看着《坡》上的牛和老屋,红色成了鲜血成了力量成了信念,每看一遍我都寸心欲碎。
“罗教授的油画一扫中国油画画坛几十年的沉闷空气。他以明亮的色彩和很自然的变形手法,创造出‘极鲜明的个人风格’。”这是英国美术评论家迈克尔·苏立文所著《20世纪的中国画和艺术家》中,对罗尔纯先生的评价。80年代初,我有认识他的机会,但我不敢。90年代末,我回乡省亲,听说他在永丰镇看王憨山先生的画,不记得什么原因又错过了。最后一次机会是2010年11月23日,他在娄底市明源佳程大酒店住了整整一周,在军旅作家胡建雄先生的陪同下,专门邀约女画家袁力带作品给他看看。当时,我正在袁大姐家看画。几天以后,陪同人员向我反映,罗老对袁力的画赞不绝口,说袁力的小鸡大鸡系列作品,放得开、架子好、搭配得好,总体效果很不错,不愧是憨山先生的女弟子,并提醒袁力在笔法上再加注意。一周时间,罗老拜了祖坟,看了众多亲戚,去了他上小学的陶龛学校旧址,非常怀念教育家罗辀重,非常赞赏“血性”这一校训。他还参观了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和白玉堂、云门寺等等。在湘乡壶天镇一个叫磨石头的地方,罗老指指点点,说这些红土地就是他作品色彩的源头。说上次他在这里住过两晚,画过一些画。罗老和胡建雄先生讲,他回湖南老家总共只有六七次,1962年、1975年、1977年、1982年、1999年、2004年,和这一次。
缘悭一面,须臾故人。又一个渴望远方的湖湘子弟走了。他不仅飞过了洞庭湖,而且飞过了太平洋。
2015年10月28日,罗老在家中遭遇火灾意外离世。家乡子弟第一时间长途跋涉多地,收集罗老作品。学弟尹晓奔送给我一张罗老的国画,颇有八大之风。我很感激,总算完成了一桩心事。
1975年的绝望,罗尔纯先生经历过,绝大多数的国人也经历过。
1977年的希望,罗尔纯先生看见了,绝大多数的国人也看见了。
1982年的热望,罗尔纯先生体会到了,绝大多数的国人也体会到了。
罗尔纯先生1975年到1982年三次回乡,占用了他回乡总次数的一半。1975年,他回乡时一定看见了饥饿难耐的乡亲、荒唐可笑的运动、万马齐喑的禁锢、天灾人祸的折腾。他知道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死亡。1977年,他回乡时大洪水已经发过,狂犬已经消灭,大地震已经震过,眼泪已经流干。制造混乱的人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他实实在在听到了春风怒号的进程。红土地啊红土地,鲜红鲜红的血浸透,他定格在那一刻,他的内心他的画面他的信念。1982年,他暑假回乡时,他家的一位亲戚恰好是我的师兄。这位哥们儿骑着单车来找我耍,说起他的伯伯罗尔纯就神采飞扬:“一张画一二万呢!”那个时候,我完全不相信。现在想来,1982年的罗尔纯先生目睹山乡巨变人心所归,一定是数次回乡中最为舒心的一次。
该跑的路他都跑了,该打的底稿他都打了,该泼的红他都泼了,该信的道他都守住了。
河山壮丽,春潮滚滚。
大好家园,寸心千古。
《鹅公坪》聂雄前/著
本书是一部回忆性的叙事散文,作品通过个人成长的视角,追忆了自己童年、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。语言自然挥洒、单纯明净,情感饱满深沉,人物温情可亲,写出了乡村社会的人际情感和时代变迁。这部作品有时代的印记,也有人文的关怀,以朴素、含蓄的文风,表达出深沉的情感。所写之事平实中见妙趣,困境中含有希望,有着一种历尽世事后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体悟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,《鹅公坪》还原了一个乡村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变迁史,在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中,直击了小乡村里几代人的悲欣生活,在展现真实热闹的乡村生活之余,更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,还原一段鲜活的乡村历史图景。
标签: